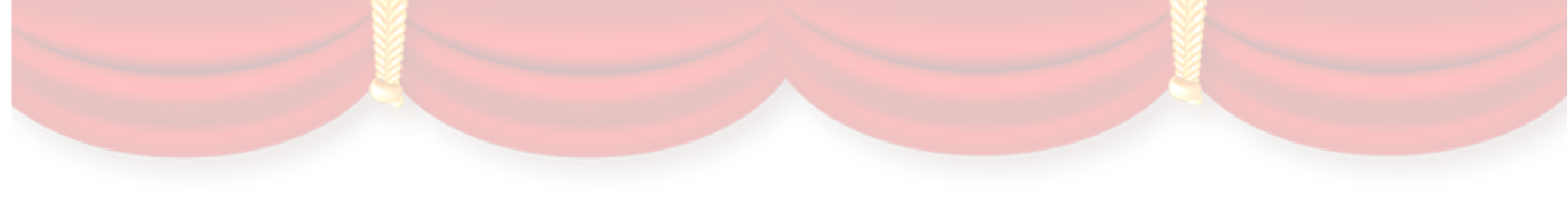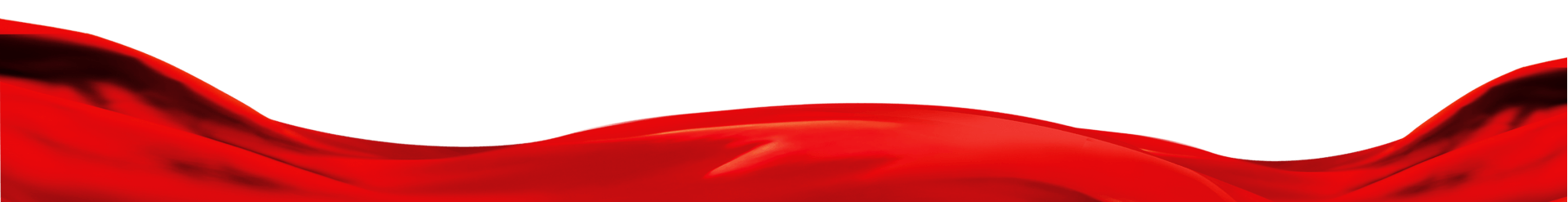来榆林出差这大半个月,我经常跟我远在广州、深圳和香港的朋友聊天,最常触及的一个话题是:在外地人眼里,榆林是座什么样的城市?
一位区域经济研究员的说法是:“可能是第一座GDP过万亿的资源型城市。”
另一位高强度冲浪人士说:“我知道,随便一铁锹下去就是煤。”接着他说起了煤老板当年叱咤娱乐圈的段子。
还有一位兄台直截了当吐出俩字:“闪开(陕K)。”
是的,想必你也能从这段浅层次的探讨里发现一个关键命题:我们榆林的城市形象,似乎有些单薄且模糊了。
从1984年宣布发现煤海至今,很长一段时间内,榆林对外最显见的印象就是“中国煤炭第一城”,这无疑让这座城市声名在外,同时也多少让它为声名所累——不就是煤都吗?有煤,有钱,这是榆林长期无法摆脱的一个单薄粗暴的标签。

但稍稍了解这座城的人会感受到,榆林的城市内涵一直都很扎实且饱满。比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,丝毫不亚于广州、南京这些历史古城,再比如它的治沙奇迹,它在民间艺术领域的煌煌大观,它滋养出来的文学“双子星”柳青和路遥……只不过,我们一直缺少足够呈现榆林这些城市内涵的途径和方法,也没有形成与老百姓足够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。
好在最近几年,榆林在这一点上的改观极为明显。
即将到来的“陕北榆林过大年”,不出意外,今年又要横扫好几个短视频平台了。只过去一年,就有“清爽榆林”、音乐节等百余项活动,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讲。这些大量的文化活动,像一个人展示他的肌理一样,呈现着这座城市值得玩味和探讨的细部。
我们还留意到,2023年以来,榆林举办了四场大型书画展,最近的一场结束在本月中旬——没错,不是榆林最擅长的秧歌、腰鼓,而是更加阳春白雪的书画艺术。这不免让我好奇:在榆林,这座很多人刻板印象里“文化沙漠”“艺术荒漠”的城市,书画展能起到什么作用?
不久前落幕的这场展名为“华夏意韵·阜美榆林”书画暨古代艺术品展,坦诚讲,我一开始并没把它放在心上。我多数时候在西安,广州、深圳也住了好几年,在这些城市,展览简直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稀松平常。直到有一天,我的榆林朋友告诉我他要跑着去看展——去晚了,人太多。我留意了一下时间,决定一探究竟。

展览的地点设在榆林市档案馆——一座拥有巨幅玻璃幕墙的建筑,光影浮动,这让展厅看上去清透且旷亮。展出的作品数量也不少,包括书法、国画、油画,足足有230余幅作品。画作基本出自全国各地名家之手,比如戴士和、孙浩。
略通绘画的人能懂得这二位在中国油画领域的分量。前者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,素来被认为是中国写意油画界的领军人物。后者是北方油画院的名誉院长,以笔触晴朗明快闻名于业内。
这些名家绝大多数都不是陕西人,但很意外,他们的作品几乎都完美捕捉了榆林的神韵,或者榆林人的神韵。比如戴士和先生这幅《榆林小伙》,画上的人阔面,浓眉,细长眼,抿嘴,微微昂着头——我每天都能在榆林的街道上见到不下二三十个类似的。

孙浩作品《波罗古堡》
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去年7月的实地采风。榆林旅投集团告诉「上郡」,不同于前两场书画展,此次展览分为前期采风、后期展览两个环节,“去年7月中旬,我们组织了十余名名家前往镇北台、红石峡、波罗古堡等地写生创作,5天时间创作了近100幅油画。”得益于此,这些画作陕北风情浓郁,意趣横生,对榆林人来讲,内容也异常熟悉。
书法作品有的是名家之作,有的则出自普通榆林人之手,我观察了一下,笔触大多豪放、潇洒,某种意义上,也是榆林人性格群像的折射。
 书法作品展出区域
书法作品展出区域剩下一个单元是诗歌,作品同样来自全国各地。策展前,榆林市人大常委会以“溪上风雅·诗意榆林”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诗词歌赋,收到1000余首作品,再经过优中选优、精中选精,最终呈现了其中90首佳作。
我的榆林朋友评价:“这是一场可以媲美之前‘绿色新榆林’文创展的展览。”
很多人应该对2024年初举办的“绿色新榆林”书画摄影文创展留有印象——迄今为止,榆林生态环境保护史上规格最高、水平最高的一次艺术展览。展览展出了325件作品,包括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文创等形式,其中69件来自省内外名家大师。
 “绿色新榆林”书画摄影文创展。图源:榆能简讯
“绿色新榆林”书画摄影文创展。图源:榆能简讯好些榆林人也是从那次艺术展才知道,原来榆林过去70年来最大的转变,不是经济,而是生态——从一座饱受沙害之地,转变为一座森林城市。这是榆林对全国最大的贡献。
举办于2024年6月上旬的“溪上烟云——十人书画精品展”是另一场小而精的展览。这场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于,它把观展空间放在了室外——绿意蓊郁的河滨公园榆阳小街,这为观众走近艺术提供了更加宽松的通道。开幕式后,主办方还围绕十位作者的创作思路、学习心得,召开了一场展览学术研讨会。
 “溪上烟云——十人书画精品展”现场
“溪上烟云——十人书画精品展”现场更早之前的展览是“长城内外 榆林市油画艺术展”举办于2023年秋天,规模相对较小,大概30余幅作品展出。这次展览类似于一颗种子,“在此之后,我们持续发力艺术展陈活动,希望能围绕书法、绘画、摄影这些形式,呈现一座更饱满、更有文化内涵的榆林。”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的人说。

稍加留意你会发现,这几场展览,都是由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牵头组织,榆林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,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联、市书协,市青年书协等单位配合,榆林驼之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障。并且几乎每场开幕式,榆林四大班子领导都全部出席——这背后,是榆林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的共识。
一场艺术展,能为榆林带来什么改变?
三年前,「上郡」曾专访了从佳县走出的国际知名艺术家、榆林渡渡美术馆创办者刘若望先生,当时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,我至今印象深刻:
“你能想象到小时候在黄河岸边赤着脚连稀饭都喝不饱的小孩,现在跟上层名流吃牛排、喝红酒吗?小时候的那些书本和画作,就像是从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点点光。寻着这一点点光,你会想走出去,想去看看世界。”
艺术展,就是这样一束“光源”。
 榆林渡渡美术馆
榆林渡渡美术馆我们反观榆林会发现,即便过去二十年它在GDP上无比璀璨和夺目,城市形象与面貌完全翻新,但在文化艺术领域,榆林的表现始终孱弱和单薄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陕北民歌歌手王二妮,她生于陕北民歌的核心区域——榆林榆阳,但学艺之路,却是始于我们的邻居延安。
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榆林当时缺少出色的艺术资源对她进行艺术素养的熏陶和挖掘。
这种艺术的熏陶,有赖于博物馆、图书馆以及艺术展这些具体可感的载体来促成。前两者榆林已经做了不少,几乎每个县区都建成了或正在建。就以靖边为例,现在靖边有一座博物馆、图书馆和文化馆,光书法和艺术培训的机构就有200多家——一个相当惊人的数据。
艺术展在榆林的起步较晚,而这正是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着力的方向。“只要能启发到那些有艺术天分、想往艺术深造的孩子,哪怕只有一个人,这场展览都是有意义的。”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的人告诉「上郡」。
 中能文化创意产业园。图源: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
中能文化创意产业园。图源: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除此之外,展览的意义还体现在对人的眼界的提升,审美的提升——通过艺术家笔触的走势和颜色的调和,站在他们的肩膀上,知道什么为“美”,什么算“丑”。
“为什么陕北有些地方会盖起来丑建筑?为什么以前我们扭秧歌只涂白脸不擦脖子?因为我们的审美观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,现在我们要往这块去做。”
可以说,这是榆林在文化运作、文化力量发掘上的最新尝试,作用到城市上,最显见的结果就是榆林的城市内涵愈发丰满——所有榆林人及外界,都能在与艺术的互动中认识榆林,了解榆林,最终沉淀的,是大众对城市的信心,对文化的自信。
它产生的效应当然不止于文化。我们知道,榆林当下正在全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,“文化旅游产业要做起来,离不开城市内涵的丰富,文化的支撑,文化的支撑又离不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。这种提升,没有10年8年看不出效果,但我们会一直做。”
待到那时,榆林的文化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大放异彩,榆林这座城的内涵和底蕴,也会在不断变化、翻新和日积跬步之中,变得更为丰富。